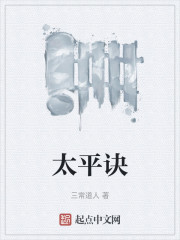
第一章(1/4)
光绪卅年,湘南大旱此时已逾两年,〝市廛寥落,闾巷无烟,徒死之余,子遗无几”。其中湖南宝庆府更是“数月不雨,赤地千里”。就连全城百姓赖以生计的资江、邵水两条环城河流都干得河床见了底,儿童们踩着邵水河中心的鹅卵石就能从上河街跑到下河街,放排的没了生计,行船的没了活路,四大码头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就连河边林立的吊脚楼妓寨都没了往日的烟火气息。
这一年的腊月廿四日,也就是公元一九零四年二月九日,我的爷爷梁俊卿一个人坐在宝庆府梁家桥梁家坟山半山腰的石头屋子里发了愁,已近年关却身无分文,最关键的是地里刨出来的红薯也没剩几根了,宝庆府有句老话叫“叫花子也要过个闹热年”现如今十四岁的孤儿梁俊卿一筹莫展,过年并不重要,怎样留口气活着熬过年关才是头等大事。
说是石头屋子,其实就是梁家坟山半山腰上的一个青石板垒成的土地庙,少年梁俊卿自幼爷死娘嫁,梁家桥的族人看他可怜,便让他守着土地庙照看梁家坟山,搭帮族长梁长满心善照顾,每逢四时八节也叮嘱族里祠堂按盈余拨点灯油余粮给他籍以度日。
那族长梁长满是行武出身,早些年入湘勇,跟随曾国荃追剿长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也爬了个营官,破南京时留了心眼,藏了一堆金银后狠心断掉自己左手一根手指,顺势退伍返乡,在梁家桥置田修宅,做了个地主。因长行善举热心公益,未得几年便被族人推举做了族长,又与县丞周宜交好,在官府里还挂了个甲首之职。
梁长满膝下只得一子,年龄与我爷爷相当,取名叫做梁恕效,字承欢。等到七岁才从白马田请了一位先生来开蒙,先生日常就睡在祠堂的东厢房,讲台就设在了东南偏房里,卯读酉毕逢五一休,我爷爷平日里拣完牛粪就喜欢趴在窗口听个新鲜,那先生就去长满那里投诉,长满哈哈一笑说:都是梁家屋里人,又有莫子卵关系?俊卿喜欢听课,就跟承欢做个伴读也要得撒。从那之后我爷爷就跟着梁恕效做了伴读跟班。
这两人对读书也没得十分的兴趣,平日里最盼望的就是午时放饭,一到午时长满家老妈子就提着一匣子饭食送进祠堂,先生吃上面的一屉,每餐必要有个一荤一素半斤米饭,梁恕效吃下面一屉,菜是一般的多,饭却多了一两。待梁恕效与先生吃完就将碗递给我爷爷,剩多剩少全看二人的胃口与心情。我爷爷拿屉子装着先生与梁恕效的碗去门前的溪涧边吃完剩饭再用水草洗得干净,最后送到长满家厨房交给老妈子,从那时起我爷爷就心怀感激,把长满认做了恩人,梁恕效也当成了舍命的兄弟。
但是腊月十五就停了私学,先生虽然还没有回去,老妈子送的饭菜却只剩了先生名分下的那一屉,那先生虽然消瘦,饭量却是惊人,每餐饭后碗刮得比水草洗过还干净。我的爷爷午饭没了着落,过得几天肚子里就彻底没了油水,生吃的红薯更加不能抵饿,越吃越怀念那碗沿粘糊糊的油荤。一想到油荤少年梁俊卿禁不住摸了摸咕咕做响的肚子,咽下一口口水,站起身来勒紧裤子,打着赤脚去给先生洗碗去了。
我爷爷从坟山晃晃悠悠地走到祠堂东厢房,那先生果然已经将饭菜吃得干干净净,看着门边眼冒金星的少年,先生斜着眼冷笑了一声:何滴?想恰饭啊?我爷爷涨红了脸,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
“看你造孽”先生抓起了桌子上的水烟壶,噗的一口吹燃了草纸揉紧的火捻子说“我今天免费教你一个赚钱的把戏,你要学莫?”
我爷爷如同一条见了骨头的土狗一样,一个箭步跑到先生面前舔着脸说“要学要学”
那先生咕噜咕噜的深吸了一口水烟,从身上掏出了五个铜板扔在桌上“我借你五个铜子,你带到城里去,到东关桥边上买一挂炮火,撕个几十段,再到摇铃巷对门的三官庙去找那道士讨个几十张红纸拓印的财神菩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