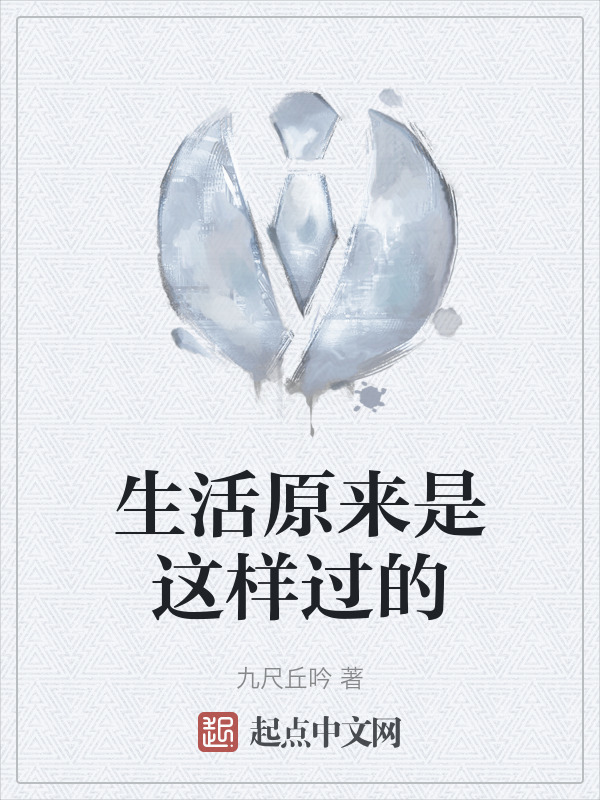
只希望下一趟的航班会延误,但它却仍旧准点发车.(1/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
小时候满腔热血,想游尽大江南北,闯遍慢野金山。可长大了,父母也年老体衰了。
曾经一则新闻这样讲的:“男子见卧床不起的母亲,痛拍胸脯,可为了工作,又扛起了沉重的行李,血泪横流,可一面是父母,一面是以后的生活,他不得不去选择…”
小时候,我也烦闷,总觉着被一直关在村落里,啥事面也没见过。大了,便心底郁闷,难得次外出机会使我撇下了家里的纸牌、雪糕,去了海南,从那刻起,我想远行!想出国!
可心有余悸,我去了,在这炎热的夏日里,谁又陪爷爷谈天论地,谁又陪奶奶做这个家务活呢?
想着想着不觉着也要去离家遥远且陌生的城市读书、工作了、独自面对生活所迫了。
“在外面做什么都要花钱,只有在家才是免费”—“妈妈都二十岁”。忽地明白这些后,原来我也跟他们一样,忙不迭步道工作、大口扒饭,然后赶紧睡觉,第二天再早起。
高铁票买得频繁了,坐得厌恶了,连着窗外皆是一片海川,但总归还是得做这个“陪客户的劳工”。
“赶快忙完工作,赶快结束学业,赶快下班,这样就能赶上下午或晚间的班次,这样就能早早回家。”我心里暗自想道。
依稀记得有次出去玩儿,回来得晚,错过了下午的班次,等到了晚间。爷爷打电话问:“今日还回来的么?”
“还回来的,您也早些休息吧~”我挂了电话,不停抚摸着冻得蜷缩的腿,茫然的瞅着玻璃门外的大巴车。原来大巴发车是那么的慢,离家乡又是那么的遥远。
夜路上,我不敢抬头望向窗外,阴风袭来一片死寂般的雾霭,又梦回到了那每周五回一次家的日子,可那时的风吹在身上明明很温馨呐!
有农民丰收的畅谈、乘客的高吭及淡淡的抹云,虽有些许寒意,但心始终是热的、紧张而又激动的。
可现在,又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呢?
到家后,奶奶依旧坐在巷子里,身上套着好几层破旧的厚毛衣。见我回来,还撒泼道:“早说就不等你的!还只把给我冻坏了,亏了多滴!要不是你王婶陪我闲磕几句,谁得住这阴风呐?话说你咋这晚才回来呀?”
“我…”—“行啦,懒得听你说这些,赶紧回屋吧,快些洗了睡,少熬夜啊我跟你说。”
说完,那时的心该有多内疚呢?所以下了决心,不管以后工作与否,要么离得远远儿的,要么寸步不离。反正——记得多给家里打打电话,打勤点儿。
可越往后走,工作多了,学业繁忙了,回家的机会成了买奖券、掷色子,回家的路有了周期,家乡,也模糊得认不太清了。
我依稀记得,我似乎回去过那么几趟,后屋的杂草生得比从前高了。不出意外的话,村子里会有死一般的寂静,如同人永远地、永远地咽下了那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