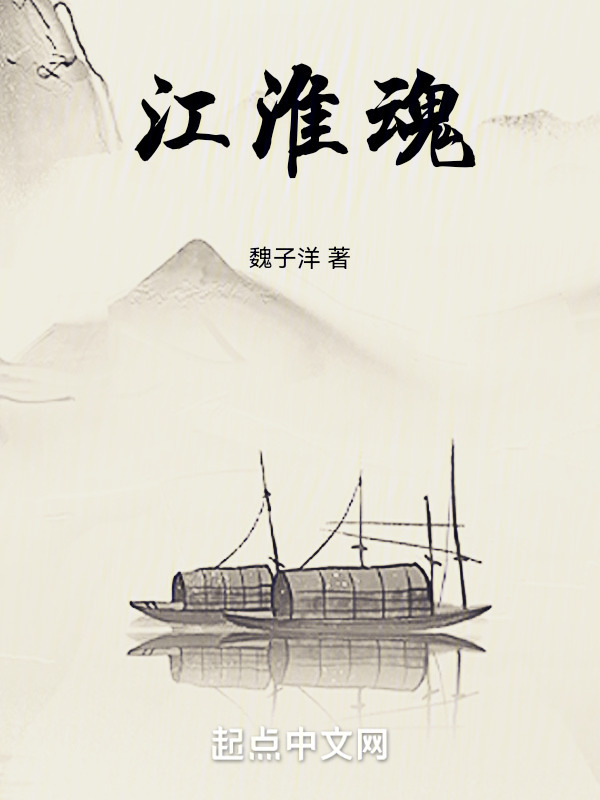
第一章(1/6)
山东莱芜的一个小村庄,本来清朝那些官老爷给村庄命名枣儿庄,后来说也奇怪,本来在当地人口几乎没有的刘姓,在明朝南移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并且东北王李自成和清兵狗咬狗地打作一团,无瑕对此地征重税。原来在天津定居的刘姓拖家带口赶过来,在当地聚集。
枣儿庄依山傍水,山峦不高,略露棱角,挡在它的背后,把秋冬吹得“飕飕”的风挡了大半截,还有一小半稀稀落落才萧瑟瑟的从那山缝中渗出来,这是得天独到的,让其居住的百姓获得了更多的良田、桑竹还有那丝甘甜的泉水。一个浅浅的小潭就安稳地躺在田野两旁,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散落着流水冲蚀过的花白石子,有红红艳艳的玛瑙石子,还有些深沉的黑色鹅卵石,那些鹅卵石就好似官场里的人们,被磨却了棱棱角角,安安心心地躺着,静睡着。水中游鱼来来往往,仿佛飞翔在浩瀚的星空,自由自在。两岸是那低矮而叠置得整整齐齐的山峦。先人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此地在获得上天如此体贴的照顾后,繁衍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庄稼人。那些老实的庄客们,春日里在顺着潭水流出的一条小溪旁播种犁地,宛若一头温和而顺从的水牛;夏天男人们就在那耀目的日光下收获着粒粒的金黄,女人就砍下些翠绿细竹,做些小巧玲珑的竹篮,为了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又绑了些麻和睡觉掉着的头发。秋冬来时,那些小屋的景象无不朗然入目、又随了些乡土的粗犷气儿,泛着些许嘈杂和浮躁。黄色泥巴砌的墙,乌色泛青的瓦,滞带着美观和自然,再与四围环境稍作调节,使人难掩活着的喜悦。
在此地的刘姓好像获得了上天的庇护一样,在此地定居后,怀上的孩子十有八九都是男孩儿。在那个封建时代,刘家人口多就是代表劳动力丰富,很快从佃农发展到中农,又很快把全村庄的土地都占有,成了远近闻名的地主。
世世代代一过,这枣儿庄便自然而然成了刘庄了。
刘庄有一大户,良田百余亩,从刘家屋旁望去,家中祖屋也很阔绰,用那青瓦砌的穹顶,屋架也是用几层玉米糊粘起来的,就如那充满韧性的藕丝一样,风刮不断,雨冲不垮,他们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勤勤恳恳、老实巴交,都说富不过三代,他们家往上数能排到南明时代,算来也有十几代了。
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个夏夜,刘府一个婴儿呱呱坠地,那日恢诡谲怪——早晨还是晴空万里的,快到正午的时候,骤然狂风大作,天上下起了暴雨,那雨下得就像水缸里随意倒出来的一样,一会儿多,一会儿少。然后这刘家的小妾鼓了十个月的大肚子突然来了一阵强烈的反应,疼得死去活来,发出尖叫连连。
“二夫人!——快生了……快找村门口接生婆啊!”家里的下人李四向门口呆若木鸡的赵五喊道。
不到一会儿,拿着黑色大木桶的接生婆便出现在门口。
接生婆是农村古老的习俗,叫过来的通常都是些年过半百的老妪,农活干不了几亩地,年轻时也没学什么针线活儿,只有干接生这种能领一篮喜蛋的活儿,谋求一些生计。
这个接生婆被称为“王接生”,之前小村儿的居民老是一口一个“王婆”地叫着。
王接生由于小的时候看过戏班来到小村的表演,耳濡目染了那段《水浒传》中潘金莲的戏儿,她总是撇了撇嘴,“小狗崽谁敢叫我王婆,我不撕烂他的嘴!”后来因为她一直为村里人接生,干脆村里人就统一口径叫她个“王接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