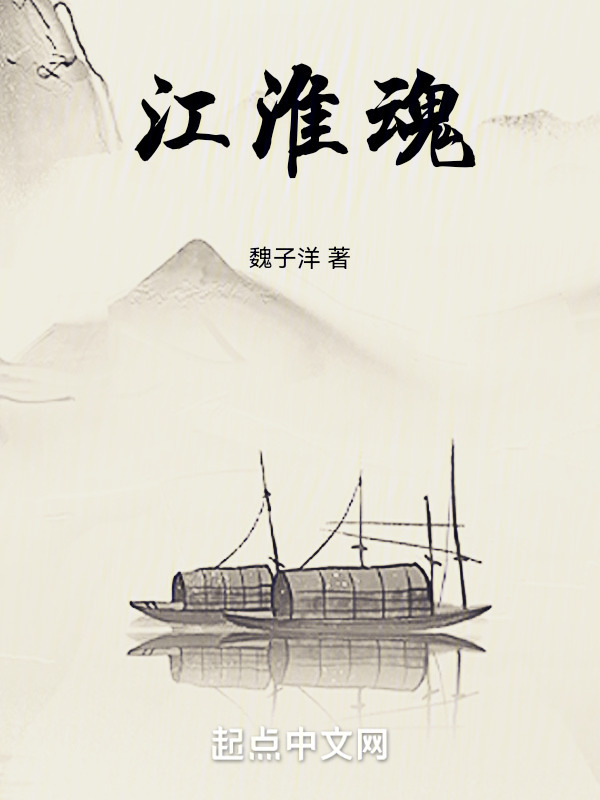
第十八章(1/9)
1924年古历八月十二日,就是倪思忠入通城的那一年,刘云兰难得圆滑了一下,花了点银两打通了守门的两个侍卫,又把自己和那九岁的李桂芳乔装打扮了一下,装作乞丐就逃了出去。
李桂芳命中的两次劫难都逃过去了。一次是从那满是鲜血的李府里逃了出来,一次是抗日战争乔装成卖报的男人躲过去了J国人的搜查。她可能还有多次伤筋动骨她都没有跟子孙提及,可能不是因为她想不起来了,而是她觉得没有必要阐述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这是生在和平年代的人永远无法想象的。
在那清冷的夜里,半盏月亮已被那黑云严严实实地挡了起来。风利飕飕地刮着,寒冷入骨,犹如一把锋利的利剑往她那低平的衣衫里捅了进去。一个身着单衣的小女孩,默默地站着,瑟瑟发抖。她望着满屋子的尸体,有她亲人的,也有侍从的和那些起义英雄的,那些鲜血都凝作了紫色,黑的糊的已经看不清了。
她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她捂住嘴巴,尽量不要因为那腥臊的尸臭而呕吐出来。
她拼命跑着,跑到了熟识的余大夫家,那里空空荡荡,余大夫被倪思忠“请”去了,做了给李思兴凌迟止血的止血大夫;她跑到了她经常吃的猪肉的杨三儿家,那杨三儿也被“请”走了,在倪思忠家磨刀霍霍,做了勾走李思兴人间魂魄的无常。直到她跑到了刘云兰家,那里面住的人是她姐姐即将要嫁过去的新郎,也是世事无常下惨剧的亲身经历者……
多年后,耄耋之年的李桂芳躺在病床上跟她的孙女、孙女婿、重孙子还会时常言语着:“我九死一生啊!稍有不慎,你们就都没有了。”
事实的确如此,没有她,何来她的子孙呢?
出了通城后,她随着刘云兰向南逃啊逃,和那些北上的难民一样,灰头土脸的,好似从烟囱里探出脖子的鹌鹑,染黑了那本应该洁白如雪的面容,但烧黑不了那冰清玉洁的心灵。
他们看到了城墙上告示上有他们的名字,皖系军阀开始通缉他们来了,他们不敢走通往城镇的大路,反而走些山道小路。他们问着来往的村民,在泥泞高山上艰难跋涉,一爬就是几里路甚至十多里。李桂芳的双腿在呻吟,仿佛两只不听使唤且灌满水银的铁铅,在那里吃力地小幅度摆动着。那双布鞋也早就湿了,甚至还磨出了不大不小的窟窿,像被老鼠蛀过的米袋,往外渗着脚汗味儿。每前进一步,鞋子都要咯吱作响。对于一个仅有九岁的女孩,这次逃命的行程,着实是举步维艰。
平日里,而无论是李桂芳怒目而视,还是小声抱怨,刘云兰都不为所动。他会挥挥手,示意她赶紧走,好到前面的村里歇一歇,刘云兰行走时是不言语的,他意志坚定的恐怖,像个时刻运转的机器,一直保持着在李桂芳前方一二米左右的距离。偶尔她绊倒的时候,他会把头扭过来看看,然后背起这个满面稚气的小妹妹,继续往前走着。
然而一旦刘云兰确定她没事了,又会放下李桂芳继续向前走去。
倒不是刘云兰决绝,而是在逃亡的过程中每多提一斤一两的物品,那体力消耗都是惊人的,就好似人在快要咽气时突然捅了他一刀,悬崖峭壁吊着的人,给了他一脚,都是致命的。
李桂芳低头望着脚下的萋萋荒草,草地上的洞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像麻子脸上难以遮掩的瘢痕,各种奇形怪状的歪歪扭扭土块又仿佛粗细不一的绊马绳,它们扭曲着蜿蜒着,尽了全力要将她绊倒,她尽量避开这些地方走,但依然徒劳。她轻声细语地哀叹几句,那是劳累的声音,她又继续步履沉重地跟着刘云兰走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