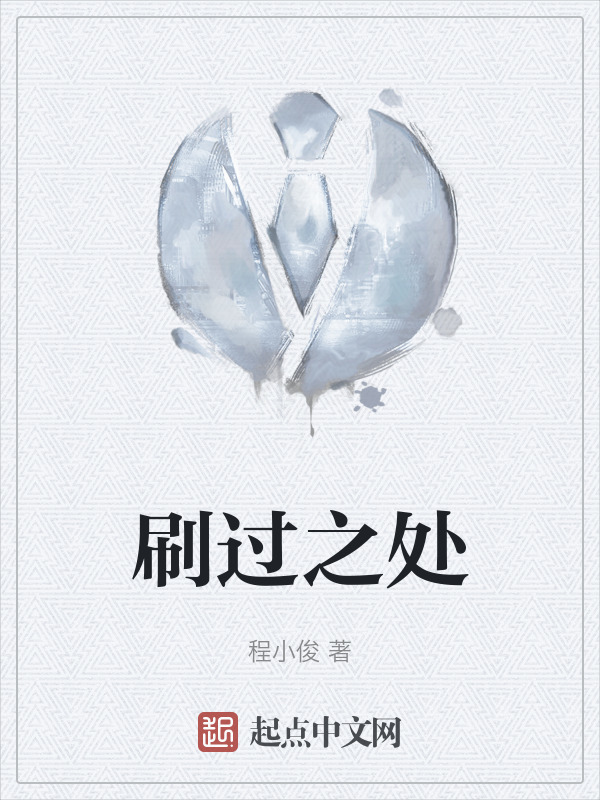
第一章(8/8)
结尾,他说道:
“当你进行了这样的一番思考后,再回过头去看待这种形式,注意,我只是说关于你自己和这种形式的联系,并不涉及他人,更不能代表该形式的整体,仅仅是对你而言,会不会产生属于自己些许新的看法呢?”
他说完了,我沉默了。老实说,我没有想过这些,应该说想过一丁点儿,但是没有这么“大”。这似乎达到了一个高度,一个我只能驻足遥望而无法攀登,也不敢攀登和不愿攀登的高度。
我有好几秒钟竟忘记了呼吸。保持着双腿分开,身子往前佝偻着背,双手肘抵在膝盖上方,手捧捂着嘴的姿势。有点像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创作的《思想者》那样,不过我是两只手。脑袋里思绪混杂,眉头不自觉地往内深蹙——感觉中间的肉都被挤得凸了起来。我也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表情,可能那样子看起来会觉得带了三分痛苦和五分困惑再加上二分茫然吧!调整了下呼吸,摆了摆头,发现阿泉和阿航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坐到了旁边。
回家的路上,想着刚才的谈话,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想要马上做点什么事情的冲动。想从桓哥的话语中寻觅一点启示,我一段一段复述,逐字逐句咀嚼,但他的措辞那么严谨,那么小心翼翼,每段话都加了很多限定词作为前提,让我不得而知。继续思考下去,竟然发现那些限定词如有生命般扭动了起来,一个接一个地跳出了当时的语境,跳出了对话框,然后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捆仙索,将我如即将脱缰的野马般的冲动牢牢地束缚住了。
我看了看旁边的阿航,一脸的慵懒与满不在乎,好像刚才的一切在他心中未曾荡起一丝波澜。难道是他的思想过于深刻,以至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
“诶!你有什么感想?”我问他。
“你问我?”
“嗯!”
阿航沉默了下,没有马上回答。他继续走着,皱着眉低头看着脚下这条小区的主路,接着视线逐渐拉远,一直看到前面的尽头,路从那里拐了个弯通向大门。然后他说了句相对他平时来说算是很长的一句话:
“你看到的、听到的,是不是真的就是你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是不是真的就是你想看到的和想听到的,是不是真的就是你应该看到的和应该听到的,你所关注的,是不是真的就是你想关注、要关注、必须关注的,还是‘被让关注’的。”
“应该是想让我们确定这点吧!”他停顿了下,加了这句。然后自己先走进去了,留我一个人站在路中央。可能是为了烘托气氛,空中下起了雨(或许是一直都在下,只是我没注意到),细雨飘飞洒落在我的头上、脸上和手背上,我仰头望向夜空,透过路灯映射下影影绰绰的雨点向上看去,不见月色和星光,只感到一片浑浊,就像我脑袋里的东西一样浑浊。
我忽然感到一种陌生感,怀疑自己是否认得面前这个人,仿佛这个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他。或许,自己从来就没有真正认得过谁。又或许,每个人原本就有很多个“面”,但由于时间、场景、心态等诸多限制,往往展现出来的只是其中一面,而我们就以这仅有的一面来认识对方,来理解对方,久而久之便把此当作了完整的面。当某一天,对方的其他面展现出来时,我们自然会有所“反应”,或许愤慨、或许心痛、或许惊奇、或许无助,多的是指责和埋怨,少的是理解与包容。
